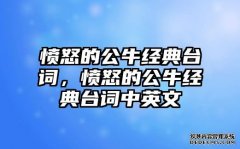武汉|十一假期特辑|「放映103-104」无限的叙述:若尔格·雅科梅作品集
武汉影像艺术中心(WPAC)以公共教育为根本,开设“在场”“焦点”“逐帧”三个公共项目系列。通过讲座、论坛、研讨、放映及映后分享等多种形式,推动影像艺术走向公众。
“在场”系列联动扎根本土的艺术文化领域工作者,梳理、建构武汉在地的艺术生长场域;“焦点”系列聚焦新兴的艺术力量,致力于为青年、新锐摄影师提供无差别的平台;“逐帧”系列则关注独立电影、录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试图探究影像艺术不断扩张的边界。
“Free-Frame自由影像”隶属于“逐帧”系列,旨在推荐和放映与传统叙事有别的先锋、实验电影与导演,拓宽本地观众对影像边界的理解。


与雅科梅作品的第一次相遇是在2021年的葡萄牙影展,《花之岛》与《过去的完美》连放,完全被其中的想象力打动。今年《超自然》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放映,也让我看到了将其带到国内的可能性。整个回顾展映将分成两个部分,十一假期我们先带来《超自然》之前的五部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无限的叙述”是阿Pin想到的标题,非常贴合几部短片的气质,“无主体”与“无法形成闭环”的结合,造就了“无限可能的差异”。从处女作《冥王星之恋》开始,旁白一直是雅科梅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常被他借来表达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这种形式不断演化,与游离的机位(《客+主=鬼》),极简音乐(《花之岛》)与超现实的景观(《无止境的派对》)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迷幻的感官体验。
在五部影片中,《过去的完美》是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作。在这部作品中,人声退去,字幕成为创作的一部分,由“有声旁白”转向“内心独白”,真正唤醒了语言和认知系统之间的关联,让人想到丹尼尔·艾森伯格(Daniel Eisenberg)的《部件合作》(Cooperation of Parts,1987)或本·拉塞尔(Ben Russell)的作品,但雅科梅显然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伴随着“无声的叙述”,我们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回到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回到最后一位威尔士王子被处死的日子,回到白垩纪第三纪,毁灭与新生的起点。我们不自觉地用话语与哼唱回应,我们的声音填补了失语的历史,这种交互便是叙述的无限。
*本次放映已获得导演授权,仅为分享交流,两天的放映都需使用小程序报名参加。
若尔格·雅科梅(Jorge Jácome)出生于1988年,是一名居住在里斯本的电影人和艺术家,他出生于葡萄牙的维亚纳堡,在澳门长大。2010年,他在葡萄牙里斯本高等戏剧与电影学院(Escola Superior de Teatro e Cinema)的导演与剪辑专业完成了电影学位;2016年,他在Le Fresnoy法国国家当代艺术工作室(法国图尔宽)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并获得了“评审团奖荣誉”。
他的作品以强烈的直觉和感官过程为基础,并以此而产生由叙事的迁移、意想不到的关系和不寻常的遭遇构成的电影,他的作品模糊了纪录与虚构的界线,探讨了乌托邦、忧郁感、消失和欲望之间的关系。
他的作品曾在许多电影节和展览中放映,荣获多个奖项——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纽约电影节、第25届美国FPS国际短片电影节、温特图尔国际短片电影节、里斯本独立国际电影节、维拉德康德国际电影节、布切斯特国际实验电影节、东京宫博物馆(Palais de Tokyo)、MoMA当代艺术博物馆、西班牙Tabakalera国际艺术中心等。
在担任电影制作人的同时,他还为其他电影人的项目进行剪辑,并定期参与表演艺术项目的合作。


科学家告诉我们,冥王星不再被视为行星。教室和博物馆商店里的海报被换掉了,与冥王星相似的新天体将继续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习惯这种想法,就像我们忘记旧情人,憧憬新天地一样。
失望与怀旧的感觉,以及无法回到生命中某些时刻的感受,让人想要从大卫的故事中找到答案,来解答科学与理性之外的东西。

《冥王星恋人》非常有趣和独特,这部电影集多种类型于一身,它融合了一种似乎是从科教电影中提取的旁白(只是又转换成了一种更加自白式的语气);它使用了一种伪纪录片的形式,让人想起“直接对着镜头讲话的头部特写”式的镜头风格,也增添了一丝科幻的气息。所有这些帮助了电影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一个“男孩遇见女孩,然后男孩失去女孩”的夏日故事。十年后的今天重看这部影片,我最感兴趣的是若尔格·雅科梅作品的核心已经在这里显现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不连贯和羞涩的感觉。从《冥王星恋人》开始,他作品里强烈的浪漫主义只会更加突出,并与他对科幻元素(尤其是天文学)的偏好相结合,一切都通过纯粹的忧郁气质融合在一起,在其中记忆构成了未来的基础。尽管《冥王星恋人》略显粗糙,而且非常天真,但它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Ricardo Vieira Lisboa)
这部充满着麦香薰衣草气息的科幻伪纪录片,既是对生态末日的梦幻想象,也是一个温柔的酷儿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岛上长满了无尽的紫色绣球花。这部带着好奇的虚构电影,生动地描述了岛上的生活、爱情与劳动,岛上两名士兵用画外音讲述了在他们居住的亚速尔群岛的一座孤岛上绣球花过度繁盛的情况。
在一场生态危机中,亚速尔群岛的居民因绣球花的肆虐而被迫迁离。两名年轻的士兵被其中的美丽风景所吸引,带领我们并讲述了那些背井离乡的悲伤故事,那些岛屿住民内在的抵抗冲动。电影中的漫步变成一种怀旧与政治反思,关于领土归属和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在自己的故乡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叙述者和与他结识的两名在岛上工作的年轻士兵的眼睛,《花之岛》创造了一段超现实而温情的浪漫故事,该片评论了经济移民、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文化丧失等现实问题。雅科梅的短片都使用了其图像和叙事策略来激活我们的想象力,对历史进行探索并使其恢复生机,同时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同理心。(Irina Leimbacher)
雅科梅深受克莱尔·德尼的影响,这部电影的政治性以及许多图像都是《军中禁恋》(Beau Travail,1999)和《入侵者》(LIntrus,2004)的第二代翻版,我在此表示由衷的赞美......《花之岛》提供了一种令人着迷的观影体验,就像德尼更为抽象的那些作品一样,它带来了遐想的逻辑和华丽的幻象,堪称这位导演的标签。(Darren Hughes)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为会对大自然造成不良影响。《花之岛》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它观察的是一种植物从人类的蚕食中夺回领地的情景,我们可以从视觉画面的淡紫调(可以看到约瑟夫·康奈尔的《罗丝·霍巴德》[Rose Hobart,1936]的影子)上看到这一点,甚至连大气都被绣球花占领了。关注到我们自身的、非常真实的生态失误,雅科梅用推理小说的方式来询问我们打算如何在紫色的统治下生存下去。(Michael Sicinski)

自从亚速尔群岛引进绣球花以来,这种植物就一直在那里繁衍生息。在若尔格·雅科梅这部短片的世界里,绣球花完全占领了岛屿,并驱赶了大部分其他生物。这构成了植物向的“男人执行任务”式科幻类型的背景,两名士兵在花瓣覆盖的荒野中出发执行任务。雅科梅通过将他们的旅程变成一个爱情故事,来进一步扭转观众的期待,将军旅情谊中的同性情愫推向了极致。生动的薰衣草色调和鲜花覆盖的场景,让这部小短片看起来比大多数耗资数亿美元的大片更具异域风情。(Dan Schindel)
若尔格·雅科梅的短片《花之岛》融合了纪录片与奇幻元素。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了,到来的不是核灾难,而是一场自然灾害。正如雅科梅讲述的那样,绣球花是亚速尔群岛最初从国外引进的一种花卉,后来在一些岛屿上蔓延开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挤走了当地的植物。在雅科梅的未来主义场景中,由于植物入侵,两名年轻的葡萄牙男子在亚速尔群岛担任军事职务。然而,影片的第二部分以法语叙述,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看待这场灾难的狡猾视角:有些人看到的是世界末日,而另一些人(在本例中是指蜂蜜生产商)看到的却是提高产量和增加利润的机会。《花之岛》镜头华丽,大量的画面都是盛开的紫蓝色绣球花,它最终呈现为一个伪装成科幻片的成长故事:这两个年轻士兵是挚友,他们通过凿刻出朋友的名字来打发时间。虽然快速查看可能会证实绣球花的故事的确是真实的,但叙事中的“瘟疫”和未来主义以及被俏皮地构建的空间则是另一回事。(Ela Bittencourt)

我们用葡萄牙青年导演若尔格·雅科梅创作的这部令人陶醉且独特的花卉短片来迎接春天的到来。在他这部混杂了超现实、浪漫元素和灾难类型的影片中,偏远的亚速尔群岛的居民为了躲避绣球花的入侵而逃离,岛上只剩下士兵、养蜂人和一位纪录片导演,他们像是在梦境中漫游。
在整部影片中,雅科梅将真实与科幻、纪录片与诗歌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亚速尔群岛的自然灾害由来已久,围绕着这些灾害的文化、传统和仪式,与导演自己的痴迷和猜测相结合,并涵盖着从酷儿乌托邦到世界末日场景和对紫色的运用等内容。
若尔格·雅科梅提到,“其中一个没有出现在电影最终剧本中的想法是,一些吸食过干绣球花的人证实了他们所经历的致幻效果。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希望影片有一种梦幻或迷幻的意境,让人陶醉在繁花之中。我认为紫色能带来这种效果,就好像镜头捕捉到的花朵的颜色给胶片也上了色。”
剧本中一直都有军队的影子,而在亚速尔群岛考察时,雅科梅遇到了佩德罗和安德烈,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士兵和好朋友,他们最终在虚构的背景下有力地扮演了自己。导演被他们的敏感和温柔所打动,这与人们对军人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雅科梅所说,“我想创造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情境,让爱和善意最终获胜,很明显他们也会实现这一点。”(le cinema club)
《客+主=鬼》是雅科梅在法国重要的电影学院和艺术研究实验室Le Fresnoy学习期间创作的作品,该作品以马塞尔·杜尚1953年的一句箴言为基础,利用自己的双手以及独特的表达能力和感官知觉进行创作。在一系列的画面中,雅科梅通过一台徘徊移动的摄像机(像幽灵一样?),运用扭曲的形式以及视听操作,以感官呈现主观性与对意义的重构。按照杜尚的主张,雅科梅邀请我们(“客”)在他的电影(“主”)中寻找体验非物质光谱的必要元素。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片名(几乎就像一件赝品),是因为影片的展开方式:由图像和声音组成的帧的总和,当图像与声音放在一起时,才会产生其他的含义。影片中没有故事,只有由电影提出的联系,这些联系的起源是直观的。

使用剪辑作为工具,我们开始求解方程,直到得出最终结果。我们在这些联系的奥秘中迷失了自己,然后找到自己。这部电影几乎是数学的,就像杜尚的游戏:星座连接着我们身体上的点,我们手上的纹线与古代石头上刻的纹路相同,目光迷失在幽灵般的梦境之中,死去的动物变成了讲故事的人。

这些影像代表了我们所知的时空裂缝的概念,它们让人联想到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并联想到在有形的东西之外另一个维度的可能性。
对我来说,电影仍然是一种工具,它能让我们看到过去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它代表了物质与精神、物理与心理、存在之物与萦绕之物之间的联系。
夜晚还年轻,月圆之夜的到来,开启了探索世界的一道门。无止尽的狂欢派对在各处举行着,人们跳起舞来,试着缩短与他人的身体距离,空虚寂寞世界里的一场冒险。夜生活结束了,迪斯科舞厅成了废墟,这个世界消失了,忧郁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这部向葡萄牙四家传奇的废弃夜店致敬的影片,展现了凝聚的力量的动人愿景。在围墙之外,舞蹈是一场无法阻挡的革命,我们只需要记住自己的感受。
这是一部实验性的纪录片,关于葡萄牙各地废弃和破败迪斯科酒吧中不复存在的夜生活。

这部短片是关于在舞池中与众多的人共舞的。这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想法,就像我们做梦时的想法一样,只有当我们睡觉时才有意义。但当我们试着去阐释它的时候,总是会脱离语境,我们无法完全翻译这种感觉。我觉得在电影媒介中,也很难将跳舞的感觉转移出来,比如我很讨厌舞蹈视频。

有观众说,转译总是会有点令人沮丧,但是通过展示一个空荡荡的、废弃的舞池,就能激活人们的身体记忆,虽然没有展示任何的身体,这对观众来说是有力和令人回味的。我明白我不能让身体出现在空间里,而只能让记忆出现在空间里,所以我开始思考能唤起这种感觉的对白。
于是我就用手机记笔记,记录一些随机的想法(比如那个舞池app的想法),还有聊天通讯工具的对话、网络上关于“如何调情”的视频。我养成了这种方法,每次晚上出门的时候我都会记笔记,而且我写的都是最平凡的事情,我不想要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或者多深刻的反思……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夜店文化对于很多社区来说都是非常具体而重要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我觉得我并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有很多人和文章可以比我更好地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想拍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创造一种可能性,让你思考这种夜生活和这些概念。
我喜欢一种站在一个想要第一次发现某些东西的人的角度的感觉,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了,那就更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需要发明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这样我就可以第一次发现一些东西。这些夜店的废墟确实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图像具有这种数字外观(有时看起来超级真实,有时只是一堆数字垃圾),所以它给人一种AI场景的感觉,像是一个复活过来的空间。
《过去的完美》是一部借用、传递和重新组合思想的电影:一系列的图像联想和想象的对话跨越了几个世纪直至今天。哪里允许悲伤,哪里才是悲伤的归宿?电影人若尔格·雅科梅创造了一种忧郁地理。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1801年创作的诗歌《渴望》(“Sehnsucht”/“Longing”)中写道:“信念和勇气是你的本钱/上帝从不施以援手/只有依靠魔力/你才能到达那片神奇的土地!”四年后,诗人去世并穿越到“彼方”,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宣称他比所谓的“此地”更接近“彼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多年来一直随身携带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甚至在流亡时也是如此。后来他在谈到这幅画时写道:“这就是历史天使的形象。(……)但是,一场风暴从天堂刮来;风暴猛烈地卷住了天使的翅膀,使他再也无法将其合拢。风暴不可抗拒地将他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一堆废墟则直冲云霄。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柏林国际电影节)

许多城市或国家都存在一种明显低迷的情况,这些地方就像葡萄牙一样,陷入了渴望过去的痛苦中。而当下的每次紧张情绪都只是冰山一角,在连续的退却中得到表现,至少退到物种的起源。在许多不同纬度地区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其往往被视为一种诊断,即对痛苦的现在的否认,而不是回到辉煌过去的渴望。(Pedro Penim)
若尔格·雅科梅催眠术一般的视频论文画面如万花筒般朦胧,对我们当今时代令人沮丧的颓废和对回到过去的模糊渴望进行了哲学式的反思。(Critrion Channel)
在这部充满幽默感的怀旧论文电影中,一位看不见的无声叙述者将对过去的明确向往与当今的忧郁进行了并置。(MoMA)
《过去的完美》从现在开始,然后回溯了几个世纪。在没有任何声音的字幕中,就像个人博客一样,我们都到了洛杉矶的一场“哭泣派对”,陌生人聚集在马尔蒙庄园酒店里一起哭泣,以获得一种“复古的忧郁”。在特写镜头中,水流在黑暗的洞穴中从长满青苔的岩石上倾泻而下。文字、图像和声音层层递进,仿佛我们能同时感知多个时间和次元。(Carmen Gray)

“是痛在哪里......?”这个问题适合作为任何电影或者对话的开场白。你会立刻被问题的核心所吸引:用语言来表达痛苦行为的困难。若尔格·雅科梅的实验性论文电影《过去的完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这部短片中,痛苦以不同的形式在过去的道路上迂回。无论如何,过去的一切都更好,不是吗?
我们回到了一个没有假新闻或者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巴西第44任总统)的时代(好像这不是同义词);那些时代一切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至少失败是可以控制的,并且不会在全球范围内给我们造成打击。我们与那些事件之间的距离,给我们用来回忆过去的滤镜增添了色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扭曲事实,忘记我们不想记住的东西,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们当下所想要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滤镜的受害者。有些人,比如圣战分子,比其他人更加极端。
“我只是不喜欢我的时代,也许只是不喜欢我自己。”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深感不满,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压抑这种不幸。佩德罗·佩尼姆(Pedro Penim是本片编剧)的诊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延伸,将这一切归咎于我们对自我形象的关注。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去看心理医生?主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在镜子中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理解我们浏览图片的方式。
若尔格·雅科梅以一系列引人联想的催眠遐想呈现了时间,在美学上让人想起早期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的电影或拉娜德雷(Lana Del Rey)的MV。这位葡萄牙导演依靠佩德罗·佩尼姆名为“之前”(Before)的精妙文本 ,该文本从对历史里程碑的修改中吸取灵感,因其独创性和紧迫的自我意识而出类拔萃。在某种程度上,雅科梅的图像(大部分)都逊色于佩尼姆的文字,由于影片类型而让电影更加突出了。
雅科梅巧妙地避开了任何画外音,并通过无声的字幕来传达佩尼姆的台词。在(所谓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例如(民粹主义的)政治领袖在浓墨重彩地描绘我们的社会时,仅仅依偎在文学中是一种宽慰。这是否意味着这首诗中所描写的神是一个进步的神呢?不。我们仍然在谈论过去以及对现在的影响......或者用蕾哈娜(Rihanna)的话来说:还有很多“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要做。
这首对过去的颂歌是如此苦乐参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某个时刻排斥它。注意了,尤其是那些怀旧爱好者们请注意了:正是同样的过去将我们带到了今天。然后,雅科梅在令人珍视的悲伤中找到了救赎,“最受虐待、最可耻的表达”是:应该在更多的时候迎接这种悲伤,这时我们就可以在当下找到彼此,并共同对抗对过去(有害的)渴望。
这种时候的净化作用可能会让大门敞开,为即将到来的时刻洒下更明亮的光芒。如果“过去”是如此“完美”,那么我们绝不应该从那里出发。完美在于保存,为什么我们要以神(或任何其他人)的名义,放弃所有进化的潜力和自我意识的进步机会呢?(Bo Alfaro Decreton)

葡萄牙电影机构Portugal Film于2013年在里斯本独立国际电影节文化协会内正式成立,致力于以结构化和专业化的方式,使葡萄牙电影能够在相关电影节上进行世界和国际首映,从而帮助葡萄牙电影作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武汉影像艺术中心(Wuhan Photography Art Centre)由华发出品打造、艺术家杨达发起创办;位于武汉华发外滩荟,地处汉口文化商业中心(咸安坊)。
WPAC致力于推广、普及影像艺术,以摄影为主要线索,同时触达多种媒介,探究影像“本体”的相关问题;始终将展览作为工作中心,以公共教育为根本,同时重视理论、出版与文献的重要作用。借由此,我们希望“更为彻底地开启艺术与学术、实践与理论、私有经验与人类共识之间的对话”。